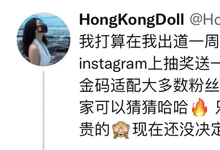这两年,在大众评价体系中,流行一个词儿:老登。
起初,这词儿还带点“解构主义”的味道,既犀利,又戏谑,泛指不尊重女性的人或作品。但把《教父》《奥本海默》等经典之作拉进“老登电影”的范畴,就纯属无厘头了。业内人士门儿清,科波拉、诺兰这些导演,再怎么“老”,人家是要在电影圣殿里“登堂入室”的,跟“老登”压根不是一个物种。
国内批判老登的风潮也势头不减,像姜文早就被点名了,不说新片《你行!不上!》怎么个“爹味”,经典之作《让子弹飞》都成了老登代表作。
最近,由于脱口秀综艺热播,衍生了新的老登群体——比如马东、罗永浩等老辈喜剧人。这让自认“女权男”的罗永浩破了大防,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波论战,围观下来,也不知谁赢谁输,暂且不提。
当然,之所以诞生“老登”这个词汇并风靡,是因为无论中外影视圈里,“老登”确实多(比如掀起METOO风暴的好莱坞大佬哈维·韦恩斯坦)。但,绝非上述经典电影和其执导者。
要说眼下活跃的“真·老登”华语电影导演,还真有一位——
王晶。
且不说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三级片的集大成者,最近一两年,借助短视频平台输出很多言论,颇也令人侧目。最新一例,是7月中旬他对梅艳芳的评价。
当镜头对准,话筒递上,磨皮滤镜开到最大时,这位自诩看透了香江风云的“讲古佬”,如此评价逝去20余年的“香港女儿”:“天分非常高,演什么像什么,唱什么是什么,唯独就是太任性害了自己。”
言语间,似乎带着一丝惋惜,但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论断,仿佛他洞悉了梅艳芳悲剧的全部根源,并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,轻描淡写地将其归结为“任性”——
一个在商业逻辑里等同于“不专业”、“不划算”的原罪。

这种论断的虚伪性,在他对其他艺人的双重标准中被无限放大。
他将初出道的张柏芝比作“又一个梅艳芳”,标签同样是“任性、天赋高得可怕”。看似夸赞,实则暗贬。然而,当话题转向当下依然炙手可热的刘亦菲时,王晶的口风陡然一变,溢美之词不绝于口:“她(虽然)不是天赋型的……她是慢慢磨炼出来的……现在她观众缘很好!”
言外之意,如今的流量密码、神仙姐姐、一线女星刘亦菲绝不像要么过世、要么过气的“前天后”那样“任性”。
这番“看人下菜碟”的表演,精准地勾勒出了一副“老登”的嘴脸:对逝者和过气者,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挥舞道德与经验的大棒,进行刻薄的“总结陈词”;而对当红的、具有商业价值的明星,他则收敛起所有锋芒,换上一副温和甚至谄媚的面孔。
这种极致的势利,这种只以“红不红”作为衡量言论尺度的实用主义,恰恰是理解王晶其人其事的最好入口。他并非不懂人情世故,恰恰相反,他太懂了。
他懂得谁可以得罪,谁必须奉承。
这种精明,其实就是“老登”的本性。

-“唔收得”是唯一死罪-
2003年12月30日,年仅40岁的梅艳芳因病去世。
王晶所说的“任性害死她”,是指什么?又想暗示什么?
即便是指她在演艺圈里“我行我素”,这也跟“害死她”风马牛不相及——况且梅艳芳是真的“故去”了。
当然,身处娱乐圈,“任性”或者说“我行我素”带来的后果是——赚不到太多钱。因而,在王晶用他那把金算盘拨拉出的世界里,梅艳芳的人生选择,是一次灾难性的“投资失败”——这和他对商业成功的狂热渴望,并将此奉为人生唯一圭臬有关。
在自传《少年王晶》一书里,王晶转述了“契师父”楚原的一句话,并视作至理名言:“阿晶,电影圈泡女演员不是罪,迟到早退不是罪,扮嘢摆款也不是罪;而只有一条死罪,就是‘唔收得’!”
“唔收得”,即是“不卖座”。
这句话,成为了王晶电影生涯的最高行动纲领。在他眼中,艺术、情怀、风骨,或者包括任性,所有这些在艺术家们看来无比珍贵的东西,在冰冷的票房数字面前,都显得无足轻重,甚至是一种累赘。
他的导演之路,始于最纯粹的功利。他坦言,自己之所以踏上导演路,不是为了什么艺术理想或虚荣心,而是“为了老婆大肚,愁分娩费用”。当邵氏老板娘方逸华问他是否有兴趣签导演合约时,他首先想到的是:一万元订金能解燃眉之急。
艺术于他,从一开始就不是神圣的殿堂,而是一个可以换取世俗利益的工具。这种认知,奠定了他未来几十年创作的底色。
在他的回忆录中,充斥着对票房数字的津津乐道。首部戏《千王斗千霸》就收五百万港币,是邵氏当时第二高票房纪录;《青蛙王子》收一千八百万,一举打破邵氏纪录;《赌神》收三千八百多万,打破香港票房纪录;《赌侠》收四千万,与《赌圣》不相上下 。
他仿若不是电影人,而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,每一次破票房纪录,都是对他“商业挂帅”原则的褒奖,也是对那些看不起他的“文艺中青年”和影评人最“甜蜜的报复”。
当《青蛙王子》以“屎尿屁”的姿态大胜被影评人捧上天的《英伦琵琶》时,王晶迎来的不是赞誉,而是“cheap”、“低俗”的骂名。他对此愤愤不平,斥责这不过是“一些自认为有文化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只要心中的信仰被人击溃,是会做出一些比市井无赖更无耻更不要脸的事”。
在他看来,观众用钱投票的结果才是唯一真理,而那些所谓的艺术评判标准,不过是酸腐文人的自嗨。
这种根深蒂固的“票房原教旨主义”,让他无法理解,更无法尊重梅艳芳的选择。在王晶的商业逻辑里,生命、健康、事业,都是可以被量化的资产。
梅艳芳在得知自己患病后,选择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燃烧自己,举办演唱会,嫁给舞台,这在世人看来是一种悲壮的、具有崇高美感的艺术献身。但王晶看到的不是艺术上的坚持,而是一个“产品”因“任性”而提前折旧报废。
在王晶的算盘上,这叫“非理性决策”,是资产的“不良处置”。他看到的是一个顶级IP因为主观“任性”,拒绝了更长久、更稳妥的“商业变现”路径,主动选择了“清盘退市”。他的那句“任性害了自己”,翻译过来就是:“你本可以活得更久,赚更多钱,创造更多商业价值,但你却‘任性’地放弃了,真是愚不可及。”
王晶用他的商业逻辑去度量梅艳芳的“任性”,就像用菜市场的电子秤去称量灵魂的重量,荒谬,且可笑。他不懂,或者说不屑于懂,对于梅艳芳这样的人,有些东西,比“收得”更重要。那份“任性”,是她对抗命运的最后武器,是她之所以为“梅艳芳”的灵魂核心。
但风云流散,他所熟悉的那个“江湖”,也早已改变了规则。在如今这个话语权越发多元、价值观越发复杂的时代,单纯的商业成功,早已不足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。
观众需要的,不仅仅是感官的刺激与一时的欢笑,还有真诚、尊重与共情。
而这,恰恰是王晶最缺乏的东西。

-投机者的道德双标-
当然,王晶这个名字本身,其实代表了香港电影最生猛、最草根、最商业的时代。他用自己的才华与算计,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娱乐帝国,也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观影记忆。
他对梅艳芳的轻率评论,绝非一次偶然的“失言”,而是他世界观的一次必然流露。这让我们看清,这位在名利场中浸淫了一辈子的“王胖子”,他的聪明,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的狡黠;他的成功,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投机。
他可以是一个出色的“讲古佬”,一个精明的生意人,但他唯独成不了一个令人尊敬的、拥有宽厚与慈悲的“大师”。
有网友指出:“王晶作为曾经的三级片扛把子,眼里只认钱的人,有什么资格对早逝的梅艳芳说三道四呢?” 这句话,精准地刺向了王晶的另一软肋——他那套极其灵活、为我所用的道德标准。
王晶从不避讳自己“屎尿屁导演”的名号,甚至引以为傲,因为这是他战胜“高雅”的武器。同样,对于“性感”这一元素,他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其中最经典的案例,莫过于他对邱淑贞的“打造”。
在《少年王晶》里,他曾详细讲述了如何将邱淑贞从一个玉女,转型为“性感女神”的整个过程。他发现邱淑貞“极有性感的潜质”,并敏锐地捕捉到叶玉卿“豁出去”之后反而暴红的市场风向。于是,他“建议她转型性感,但定下三点不露的原则……走高档性感路线”。
请注意他描述这个过程时所用的词汇,充满了商业策划的冷静与精准。为了让邱淑贞安心,他请来《PLAYBOY》的女摄影师,拍摄现场全是女性;他精心设计海报构图,在报纸上买下全版广告,用“玉女初露,震惊全港”来炒热话题;他甚至在电影上映前玩起了“裸背每天转多一点”的悬念营销。
整个过程,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商业包装,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:将女性的身体与性感符号化,转化为最大的商业价值。尽管最终《赤裸羔羊》在香港亏了四百万,但“捧红了一个性感女神”,这笔投资在他看来是值得的。
王晶最厉害的地方,在于他总能给自己对女性的物化行为,披上一件“为你着想”的温情外衣。他会告诉你,这是在“帮助”女演员“突破”,是“提携”,是为她的事业“另辟蹊径”。他用最昂贵的时装和最柔和的灯光,让你几乎忘掉了这背后赤裸裸的商业剥削本质。
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如何利用“性”作为商业筹码的导演,却回过头来,以一种长者、智者的姿态,去评判梅艳芳的个人生活与人生抉择。这种角色的错位,构成了巨大的讽刺。
他可以为了票房,毫无心理负担地拍摄和制作充满性暗示、感官刺激的内容,因为这是“市场需要”。但在他的道德天平上,一个女性艺术家坚持自我、忠于内心的“任性”,却成了不可饶恕的“原罪”。
这种双重标准,暴露了他道德体系的工具本质。他的道德,不是建立在普世的善恶观之上,而是服务于他的商业利益。
当低俗和性感能换来票房时,道德便可以暂时搁置;当他需要占据一个制高点去评判他人时,他又可以摇身一变,成为一个痛心疾首的“人生导师”。这种灵活的道德身段,是“老登”在江湖中安身立命的法宝,却也让他的所有“说教”都显得无比廉价和可笑。
这种双标的道德身段,是老江湖的护身符,也是“老登”的照妖镜,照出的,是空洞、投机且毫无原则的内核。

-捧强踩弱的生存哲学-
王晶的“老登”本性,最集中的体现,就是他处理人际关系时那种深入骨髓的“捧强踩弱”的势利。他的一生,都在与各种“大佬”打交道,并从中学会了一套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。
他对给予机会的“大佬”们,从不吝惜赞美之词。他盛赞邵氏老板娘方逸华是“坚韧不屈的勤奋女性”,是“极有魄力的女子”;他钦佩邵逸夫先生在商业决策上的“忍”字诀,认为其“智慧爆棚,学到三成都发达”。
王晶对将他推上事业高峰的向华胜,更是心存感激,称其“逼出了我的潜能”,“电影触觉之敏锐,今日我仍未见人出其右”。对于向华强,他则称其为“极有领袖魅力的老板”,在他旗下做事如沐春风“没有后顾之忧”。
这些描述,固然有事实成分,但字里行间那种对权势的敬畏与仰望,则显而易见。他深知,在香港电影这个资本与人脉交织的丛林里,得罪这些手握资源的大佬,无异于自断生路。
他对明星的态度,同样遵循着这套“强弱”法则。在与周星驰的合作中,他坦言两人初期“好合得来”,但随着周星驰气场改变,变得“霸气”,两人合作变得困难。然而,他并没有选择硬碰硬,而是采取了“意见不同,我问他:‘这样好不好?’‘唔好’‘你话点?’‘得,照你意思’”的策略。
他甚至直白地承认,与周星驰的合作“纯粹是商业上互相利用”。面对如日中天的周星驰,他选择了妥协与利用,这是一种面对强者的务实。
20年后,王晶无法“再利用”周星驰之后,在后者深陷人情漩涡时,毫不犹豫地加入“倒周”大军,选择了落井下石,狠狠踩上一脚,尽显用人朝前、不用人朝后的本色。
当他面对那些失意者时,态度则完全不同。在《少年王晶》里,他对演员汪禹的描述,即为一个绝佳的例子。
他先是承认汪禹曾是与成龙、傅声齐名的功夫小子,但很快便笔锋一转,开始细数其“麻烦人”、“玩嘢”、态度嚣张的种种不是。他将汪禹的堕落归结为名利来得太快、不懂珍惜,并详细记述了其后来吸毒、四处借钱、众叛亲离的惨状。
整段文字,充满了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道德优越感,将汪禹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。
对强者,他仰望、妥协、利用;对弱者,他俯视、说教、批判;对没法再利用的,则是翻脸不认人、狠踩一脚。这套法则,在数十年后的今天,被他原封不动地用在了刘亦菲和梅艳芳身上。
刘亦菲是强者,是当红的、能带来利益的“神仙姐姐”,所以他要夸她的努力与后天磨炼,这是安全且讨喜的赞美。而梅艳芳,则是无法反驳的逝者,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忌地给她贴上“任性”的标签,将复杂的生命悲剧简单化、污名化。
这种根植人性深处的欺软怕硬,在年轻时,可以被称作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;但到了暮年,当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依然固守着这套丛林法则,并将其作为向公众输出的价值观时,就只剩下“老登”的猥琐与不堪了。
撰稿 | 筱熙
策划 | 文娱春秋编辑部